来源:华夏时报
人性之恶,有时超出想象。在浙江台州,一桩由亲生儿子策划、伙同他人制造的“杀母骗保”案,撕开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角。
台州市中院的一纸判决书,还原了这起违背人伦礼法的“交通事故”。三名年轻人,为骗取保险金,不惜三次策划对至亲下手,最终在一条无监控的村路上,驾车撞死母亲。
据相关媒体报道,该案于今年4月30日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另外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程序,尚未宣判。
上海美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项方亮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保险实务中针对“关系异常”的背景调查机制存在完善空间,现有规范虽在《人身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中要求保险公司对高额人身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以及投保动机进行尽职调查,但未明确“关系异常”的具体认定标准与调查深度,亟须进一步强化“风险导向”的核查逻辑。
高额保单何以成为“催命符”
三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场历时数月、经过多次踩点、预谋与模拟,最终选定无监控路段下手的精心策划。卢某某将母亲徐某某诱至现场,由杨某某驾车撞击,程某则负责事后作伪证。
回顾案件始末,早在2023年4月,徐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卢某某与杨某某就已觊觎她的保险赔偿金。同年7月,保险公司将31万余元赔偿款转入徐某某账户后,卢某某偷出母亲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与杨某某共同将这笔钱取现并挥霍一空。
但几人并未收手,反而将骗保的念头转向更极端的方向。他们先是尝试在制造电动车事故时,用钉子戳瞎徐某某的眼睛,但未能得逞。随后,他们又将目标转向卢某某的父亲,同样计划失败。
最终,杨某某提议:“直接撞死徐某某骗保。”卢某某没有反对,而是在祖父与母亲之间,选择了母亲作为杀害目标。他们上网查询撞死人的车速、保险赔偿金额,约定事成后的分成比例,并精心策划如何逃避侦查。更令人心寒的是,卢某某的父亲在案发前已知情,却在儿子的反复劝说下,以一句“随便你们怎么样都行”默许了这场对发妻的谋杀。
法院审理指出,该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人伦,动机非常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予严惩”。
保险制度本是为保障生命与财产而设的安全网,在此案中却被扭曲为犯罪的诱因。这起案件是因警方深入调查才揭露谋杀真相,若仅作为普通交通事故处理,很可能成功理赔。这反映出,在面对精心策划,尤其是亲属合谋的保险欺诈时,保险公司常规的调查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项方亮认为,此案凸显了保险公司“单打独斗”式调查的局限性,构建跨部门协作的反欺诈网络是必然趋势。依据《反保险欺诈指引》,保险机构应当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监管机构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反保险欺诈工作机制,共享反保险欺诈信息,协同打击保险欺诈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案的准备阶段,凶手们上网查询撞死人的车速和赔偿金额。这种通过网络预谋的行为,理论上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例如,分析投保后的异常搜索行为、关联多份高额保单、核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和债务情况等。
然而,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保险专业律师李滨指出:“这些措施保险公司是需要投入的,但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鲜有保险公司在保护被保险人生命安全方面有投入技术设施和技术手段。”
项方亮认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是防范“网络预谋型骗保”的有效工具,但其应用需以合规为前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履行法定职责或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信息处理行为,可不经个人同意。
李滨进一步指出,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将死亡保额控制在被保险人年收入的合理倍数内,以控制道德风险。同时,他特别批评了目前广泛推荐甚至捆绑销售的“驾乘意外险”(从车)。
“为研究驾乘险费率和条款的公平性,我曾购买四十多家保险公司的驾乘险,累计含死亡保险金额理论上可达几千万元。任何人坐到我车辆座位上,瞬间就被强加几千万元的死亡保险。” 李滨告诉记者,如此高额的死亡保险,对被保险人无疑构成死亡威胁。”
“更严重的是,这个险种不记名、随机,即使有风险意识的人也无从查询自己所驾驶或乘坐的车辆是否购买了驾乘险,自己是否已成为高额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李滨表示,他已推动驾乘险合法经营达五年之久,目前已有部分保险公司停售该产品。
遏制保险诈骗需多方合力
“杀母骗保”案并非孤例。近年来,保险诈骗案件呈现出升级与异化的趋势,手段愈发多样,情节愈发恶劣,对社会的诚信基础和保险行业的健康运营构成了严峻挑战。
传统的保险诈骗多集中于虚构事故、夸大损失、伪造病历等。然而,近年来涌现出多起突破人伦底线的暴力骗保案。例如2017年,安徽淮北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报案者是一名中年男子高某,声称他的妻子在当地的上城国际坠楼身亡。经过警方调查,这是一起杀妻骗保案。根据高某交代,在高某与妻子结婚之后,高某给妻子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因为自己想要这一笔钱,所以用妻子的性命换取意外赔偿金。
2018年,锦州发生一起车祸,开车的丈夫周某重伤,车上的妻子死亡。死者家属事后发现多份保单,若妻子意外身故,周某可获理赔约2949万元。2021年7月,周某犯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
同样是在2018年,接连发生“泰国杀妻骗保案”与“湖南新化杀妻骗保案”。张某在泰国普吉岛将妻子杀害,企图骗取高达数千万元的意外险赔偿,震惊中外。湖南的何某为骗保制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假死的局面,实际是将妻子杀害并掩埋。
此外还有自残、自杀式骗保。部分地区出现团伙成员通过自断手足,甚至牺牲生命等方式,伪装意外骗取高额赔偿。保险的本意是保障与安抚,但高额保险金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可能成为诱发犯罪的催化剂。李滨认为,从产品设计源头,保险公司应对某些特定险种(如意外险)的保额设置更审慎的上限,并加强投保时的伦理教育与风险提示。
项方亮也认为,高额保险金确实存在“道德风险诱发”的潜在可能,保险产品设计需回归“保障本质”,在保额设定与风险防范间寻求平衡。例如,《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要求保险产品设计符合“公平原则”与“风险匹配原则”;《关于进一步规范意外险市场秩序的通知》也强调意外险产品需与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相适应。
保险诈骗已从早期的单人作案,发展为内外勾结、团伙作案的趋势。有的犯罪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有组织地寻找目标、伪造现场、办理贷款和保险,甚至打通内部环节。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跨区域流动作案,增加了侦查和取证的难度。
面对骗保手段的升级,保险行业的反欺诈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雷博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一是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保险公司之间、保险业与公安、司法、医疗、金融等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一个投保人在多家公司重复、高额投保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
二是调查权限与能力有限。陈雷博指出,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缺乏执法部门的调查权限,在面对有预谋的犯罪时,往往力不从心。三是成本与效益的平衡。投入巨资建立反欺诈系统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短期业绩压力下,反欺诈的投入可能被边缘化。
在陈雷博看来,遏制保险诈骗,尤其是防范“杀母骗保”此类极端悲剧重演,需要行业、监管和社会多方协同,构建多维度的防火墙。唯有通过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更深刻的社会伦理反思,才能筑牢防火墙,让保险真正成为守护生命与安宁的屏障,而非一道“催命符”。
责任编辑:冯樱子 主编:张志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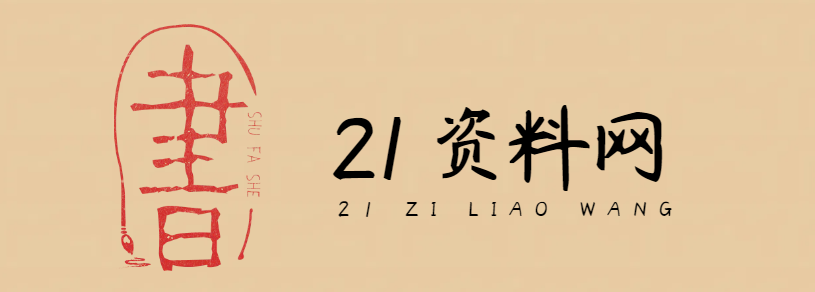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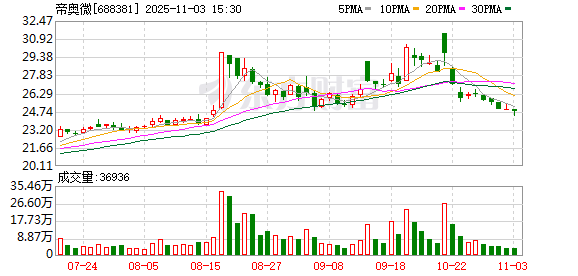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